雷格:不必远方,诗就是生活
舜网-济南日报 2021-01-23 07:35: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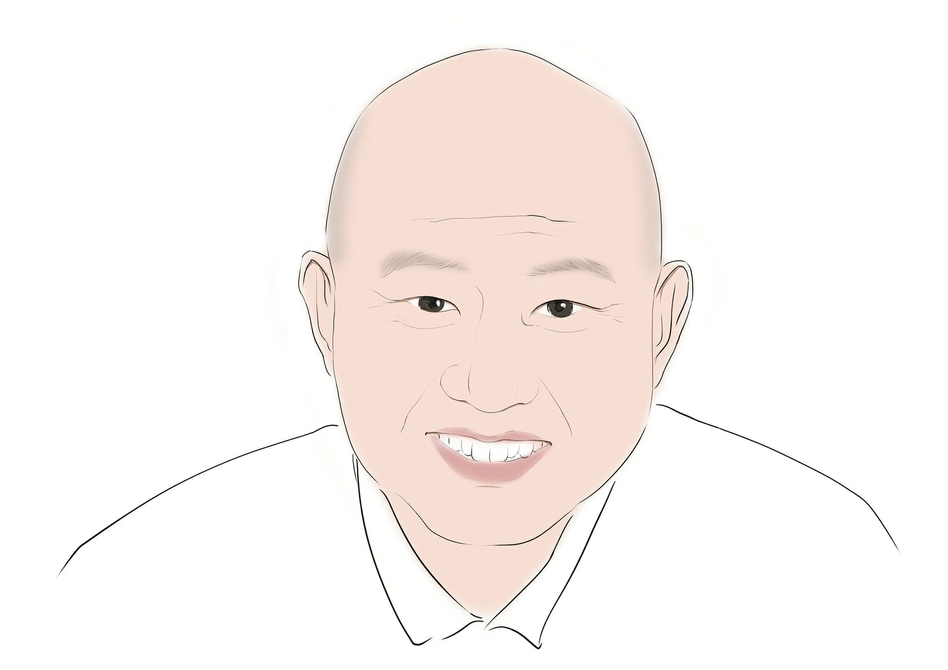
□新时报记者 徐敏 孙婷婷 绘
“凌晨四点钟,打铁,打铁,修补这个世界的不完整。”2020年1月27日,诗人雷格写下这样的诗句悼念意外身亡的科比·布莱恩特。
在节奏飞快而纷扰的当下生活中,忙碌的人们更加向往“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诗意生活。诗人雷格却说,不必远方,诗就是生活。
雷格,诗人、作家、翻译家,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致力于现代诗歌的写作、翻译、普及30余年,有《诗歌的秘密花园》《老负鼠的现世猫》等多种诗歌作品以及译著。在诗人雷格眼中,这依然是属于诗歌的蓬勃年代。近日,记者就阅读、诗歌、翻译等话题采访了诗人雷格。
诗歌是少年时期的全部世界
新时报:您曾经在访谈中提到过,中学时代就通读了艾青所有的作品。可否谈谈您青少年时代诗歌的阅读经历?
雷格:中学时代读艾青的诗,是受我父亲的影响。父亲非常推崇艾青,认为艾青是“中国20世纪的第一小提琴手”,所以家里收藏了很多艾青的诗集,也为我的阅读提供了便利。我读到的艾青的诗,不仅有他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那些名作,甚至还包括一首他写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长诗《黑鳗》。当然也包括那些“归来的歌”,《鱼化石》《古罗马的大斗技场》《光的赞歌》等。
不过那时候读得最多的是“今天派”的朦胧诗,甚至是在《朦胧诗选》正式出版之前。因为我父亲是《朦胧诗选》的责任编辑,诗选的几位编者经常来家里跟父亲讨论,所以我最初读到的是诗选的排版校对稿。记得北岛、舒婷的大部分诗我都能背,最喜欢的是杨炼。
新时报:青少年时期对诗歌是何种感悟?伴随着诗歌阅读,您也开始了诗歌创作生涯?
雷格:就在阅读艾青、杨炼、北岛等诗人诗歌的同时,我也开始尝试写诗。学习诗艺的需求增大,阅读范围逐渐扩展,很快跳过雪莱、海涅、普希金,文学口味偏向现代主义,开始喜欢波德莱尔、艾略特、阿波利奈尔、埃利蒂斯。读到《九叶集》,开始迷恋穆旦。这种文学口味的强化,和我那个时候读小说的喜好同步:《都柏林人》《百年孤独》《喧哗与骚动》,还有博尔赫斯。
诗歌于少年的我而言几乎是全部的世界,它深邃广大、无穷无尽,以我简单的心智所能领受和窥见的那一点黑暗中的艺术之光,就足以让我如痴如醉、欲罢不能了。当然,那时的我还不能完全体会生活本身的重量、意蕴,及其与诗歌水乳交融的关联,一切都需要时间。
新时报:如何读懂一首诗,您曾提出的几个建议是“信任”:信任诗人,信任文本,信任自己,信任诗歌。可否以我个人非常喜欢的诗人博尔赫斯为例,简单谈谈如何读懂博尔赫斯?
雷格:博尔赫斯也是我非常喜欢的诗人,他身处现代诗歌顶尖高手的行列,却有一个突出的个人特点,就是自然、松弛,没有什么剑拔弩张的竞技性,更像是在专注于一个有趣的游戏。我想这和他的个人经历及文学观念有关:他一辈子跟图书馆打交道、与知识为伍,后半生因为视力丧失,读不了书,这种直接联系就基本上断掉了。书籍也好、知识也好、艺术也好、荣誉也好,他都经历过“得”,也经历过“失”,所以得失心没那么重,对于无尽的黑暗也能安之若素。这是他的诗特别迷人的奥秘之一。
当然要读懂博尔赫斯,也要按照他在小径分岔的路口摆下的路标走,这是他给我们的福利。博尔赫斯自己说过,他的作品不过写了有限的几个意象,比如镜子、迷宫、百科全书等。这说明,有些主题他会反复写到,比如时间的相对性,比如历史的可能性,比如知识的命运,比如虚构与真实的界限,等等。沿着这些路子向前走,去理解他,我觉得可以说“虽不中,亦不远矣”。他写小说时喜欢打埋伏,写诗反而诚恳得多,相当直接。
诗歌从双脚踏着的土地里长出来
新时报:很多人都觉得诗歌是属于少数人的阳春白雪。您在书中谈到,“不必远方,诗就是生活”。能具体谈谈这个观点吗?
雷格:这个观点是我在解读爱尔兰诗人希尼的那篇文章里提出的。起因是那一阵子大家老在说高晓松歌词里说的——“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然后就把诗和远方绑定在一起了。这话初听好像很有道理,也很励志,但细一琢磨,又觉得有哪儿不对劲:这是把诗和生活对立起来了。
而读希尼的诗给我最大的触动是:生活永远是诗人所能得到的最伟大的馈赠。希尼长年累月地写他的故乡,写故乡的农事生活,写他的父母、妻儿、亲戚、朋友、邻人,却无损于他作为伟大诗人的一分一毫。他的诗令人惊奇地揭示了生活和诗歌艺术的隐秘联系,就是说,诗歌是如何从生活的土地上长出来的。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一首好诗允许你双脚踏地,同时脑袋伸入空中。”
前一阵子我家的猫走失了五天四夜,我一度非常痛苦和懊悔,就写了一首诗记录这件事。后来和几个诗友一起搞活动,要互相评诗,轮到我这首时,负责评价的那位朋友没有从里面读出背后的深意,竟然支吾半天,一句话说不出来。我想,这可能就关系到对诗的功能的认知吧。我从不觉得诗一定是什么阳春白雪,它再曲高和寡,也要从双脚踏着的土地里长出来。
新时报:比起当年的卞之琳、戴望舒、徐志摩、冯至,甚至海子、顾城的年代,当下我们(尤其是青年人)诗歌的写作和阅读环境,气氛是不是都弱了很多?对此,您如何看?
雷格:我倒没有太多这样的感觉。现在的青年诗人很多,也写得特别好,不过就是社会的边界扩得比较大,我们不太看得见了而已。也许你深入到网络上某个诗歌爱好者的社群会发现,原来诗的氛围还是这样好啊!诗可能会有阶段性的式微,但不会消亡的,对这个我有信心。
翻译本身就是最好的学习
新时报:阅读外国诗人的著作,您通常是读原版(英文版)还是翻译版(中文版)?您是中文系出身,如何成为了一名翻译家?
雷格:两种情况都有,目的不一样,读翻译版是为了欣赏,读原版是为了学习。还有一种情况是先读了翻译的中文版,觉得有的地方读不顺、讲不通,就去查阅原版,一看,果然有问题。举个例子,我解读20世纪外国现代诗,发现就连好些流传已久的经典译本也有瑕疵,在向读者解释说明的时候没法沿用,只好自己动手重新翻译一遍,算是为我写文章服务吧。
最近有个学姐在微信群里晒出当年我们在大学里印行的一期杂志,我发现里面就有我翻译的美国诗人约翰·阿什贝利的诗,这才想起,不自量力地翻译诗,其实从很早就开始了。后来还翻译过一些小说,大都是处于失业状态时打发时间的无奈之举,就像博尔赫斯说的:“让时光的流逝使我安心。”
还是要强调一下,对我来说,翻译本身就是最好的学习。
新时报:您认为翻译版究竟能否精准地表达出作者在母语中所表达的情愫?如果不能的话,差距和难度在哪里?
雷格:首先我要说,翻译诗无论好与坏,总有其存在的理由和价值,这是跨文化、跨语言的交流和借鉴所必需的。在这个前提下讨论翻译诗能否准确传达原作的精妙之处才有意义。
前不久有朋友坚持要我用量化的方式说明翻译诗能够保留多少原作的精华,我被逼无奈,就胡乱说了一句:“百分之七十吧。”我想,这百分之七十,主要是内容、意义方面的东西,还有一些节奏、语调上的东西;那损耗的百分之三十,主要是声音、韵律方面的东西。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语言隔阂和差异就天然地在那儿摆着呢。
不过我们还有一些补救的办法,就是用汉语里的声音替代,以补足其中的缺失。不同译文之间,往往就在这个时候分出一些优劣高下。有很多人主张由诗人来译诗,可能就是希望这种对声音的把握、这种对声音的敏感能够尽量和原作匹配吧。所以说,这时候起决定性作用的,可能不是对原作的理解力,而是驾驭汉语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