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舜网-济南时报
2024-03-31 10:36: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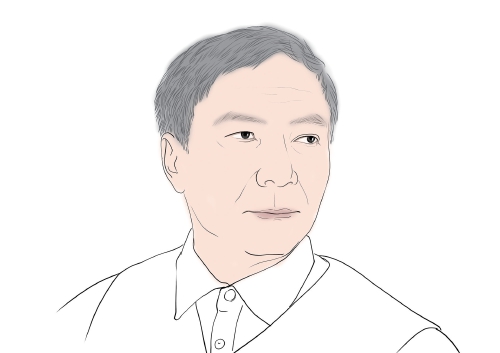
孙婷婷 绘
“人的一生,很像是可以醒在不同时空中的梦的万花筒。”
这是印在《登春台》封面上的一句话,《登春台》是茅盾文学奖得主、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格非暌违四年的全新长篇小说。
出生于1964年的格非,至今已笔耕不辍近40年,新近由译林出版社出版的《登春台》,延续了格非创作脉络中对现代文明的关切,四个充满“命运感”的人物故事,渗透着作者对中国社会广泛精微的考察,和对人性、自我等命题的绵绵哲思。
关联性
《登春台》聚焦1980年代至今40余年里四个人的命运流转,沈辛夷、陈克明、窦宝庆、周振遐,分别从江南的笤溪村、北京的小羊坊村、甘肃云峰镇、天津城来到北京春台路67号,他们供职于同一家物联网公司,又在若即若离中,展演着自己的故事。处于江南乡村家庭旋涡中的沈辛夷,在逃离与顺应中进退维谷;深爱妻子的陈克明,却不可避免地陷入出轨的危险;阴郁的“野人”窦宝庆,怀揣秘密,在人群中独行;业已退休、烹茶养花的企业家周振遐十分确认自己正处于幸福之中,对死亡的恐惧却依旧与他如影随形。
小说以四个人物的姓名为题分为四章,讲述各自的故事,并在头尾接续序章与附记两个部分。四个人物的故事既相对独立,又彼此联结。故事渐渐拼凑成全貌,带读者离开地面,回望时代。
在《登春台》的新书分享会上,格非说到了5年前开始酝酿这部小说时想到的一个核心概念:关联性。格非出生在农村,“17岁前仿佛生活在另外一个世界,基本没出过县城,和外面的世界没有任何关联性”。17岁到上海读书,后来又到北京工作,去过世界上很多地方,对“关联性”有了越来越深切的体会,“仿佛所有的陌生人都能关联起来”。但格非觉得,光有对“关联性”的体认和思考还不足以形成一部长篇。“从2019年开始,我每天都会有一个多小时的晨跑,跑步时思维特别活跃,会把很多想法记录到本子上,记了厚厚一本。真正动笔写《登春台》,用了两年时间。”
书名为什么叫“登春台”?格非说彼时自己正在看高明的《帛书老子校注》,做了很多笔记,老子《道德经》第二十章有言:“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台。”格非在笔记中写标注——“此可做题目”。而所谓“众人熙熙”,正和格非酝酿这部小说时想到的“关联性”概念密切相关,“众人熙熙”,就是里尔克所谓的“伟大的芸芸众生”,是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所谓的“他人”。
生命的潜能
人与人之间的“关联性”会编织成网,格非说,我们跟一个人打交道,会体会到海德格尔的“常人”概念,“换句话说,你面对的不仅是一个人,还有这个人背后的无形的力量”,这种力量来自制度、习俗等等规定性的东西,如果受这种规定性的制约而随波逐流,那么你将进入一种“自动化生存”状态,生命往往会因此而“纠结”,而“痛苦”。
如《登春台》中所写,“这些无远弗届的时尚信息,来自一个巨大的全球性的社会网络系统。你非要给这个无形的网络一个恰当的名称,它或许可以被称作‘他人’。而‘他人’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你追问到底所获得的答案,也许只能是‘查无此人’。很多时候,它仅仅意味着某种情绪、幻想或意愿的不安悸动,风一刮,也就没了踪影”。
《登春台》中沈辛夷的母亲贾连芳的人生,就仿佛一种“自愿接受的无期徒刑”。作家通过这对母女各自人生和母女关系的深度描写,反思了在“他人”和时代挟裹下,一种自在与舒适的生活目的的丧失。
这种反思,延伸到现实生活,会落到年轻人该如何面对各种各样的“固化”,如何面对大数据的“包围”,以及如何面对“焦虑”和“躺平”这样的问题上。为此格非提到奥地利作家罗伯特·穆齐尔,“穆齐尔仿佛是一个预言家,他在20世纪30年代写的小说《没有个性的人》中就预言将来会是一个数学的时代,人们的命运会被数据计算出来。如何对抗数据?穆齐尔说有一样东西可以对抗数据,那就是神秘主义。”
或许有人会把类似巫术的东西看作“神秘主义”,但格非认为,我们更应该把它理解为对生命中的潜能的把握和发掘,“就像托尔斯泰说的,如果把惯性当作人生唯一的道路,潜能尚未开掘就枯萎了,生命就被白白浪费了”。什么是潜能?“阿甘本认为,潜能不是我们可以做什么,而是可以不做什么。换句话说,我们要回到潜能,如此才能开启潜能”。
偶然与命运
如果不写作,会有一种怎样的人生?格非说自己其实一直都在思考这个问题,而回望人生,他看到的是人生和命运的偶然。
第一次考大学没考上,当时的格非已经安然接受了命运的安排:跟一个亲戚去做木匠,“但你想破脑袋也想不到,就在这个时候,会出现一个我不认识的人,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这个人是我们乡里中心小学的校长。这位校长听说那一年全乡没有一个人考上大学,很生气,就问别人哪些人有考取大学的希望,有人就给他提供了一个名单。”格非就出现在这个名单上,“这位校长戴着草帽,走了很长的路,晚上五六点钟才摸黑到了我们村,找到我们家,建议我去某个重点中学复读。我的命运从此改变。”
偶然性的力量继续塑造着格非的命运,大学毕业,格非被分配到江苏省文联工作,这时,同班一个同学“突然谈了恋爱”,为了恋人,这位同学决定去北京工作,而他原本是留校的,这样一来,留校名额空了出来,辅导员就让格非留了校,“我于是成了一名大学老师,命运被再次改变”。
“偶然性真的很奇妙,那些改变我命运的大事,全是由偶然性构成的”,回首往事,格非觉得自己仿佛置身“命运交叉的花园”,不同的偶然事件都会让命运走上不同的小径,这让他总是有着强烈的“命运感”,“那个时候虽然穷,虽然卑微,但每个人都充满了希望,我是他人,我有很多分身,我行走在命运交叉的花园,最后走成了现在的我”。
享受孤独
格非是小说家,同时也是教授,偏重感性和想象的小说创作与偏重理性和思考的理论研究当然存在着一定的“冲突”。格非坦言,面对这种“冲突”,自己还是不愿意通过论文,而更愿意通过“隐喻”进行思考和表达,在学术上不愿意涉入太深,而是更愿意和学生一起进行阅读、分析和思考,“做一个不一样的老师”。在这个意义上,“教授”的身份让格非有了极为重要的收获:“对阅读而言,我总是带着偏见,自己不喜欢看的作家就不会去看,但是作为一名老师,必须公允地对待文学史上的那些作家,所以就必须逼迫自己去读那些原本我不喜欢的作家,而恰恰在这个过程中,我慢慢发现,很多原来我不喜欢的作家,居然成了我特别喜欢的作家。如果不因为当老师,我将永远遗憾地错过他们。”
不过格非也坦言,眼下自己的阅读和写作都比较“节制”,“小说的重要性已经下降”,因为“很难读到真正令人激动的小说”,他认为,这也是小说创作的难度所在,“世界早已被联系在了一起,人们可以很容易地了解远方,已经没有远方的奇闻逸事令人激动了。另外,以前我们会对一件日常之物无比珍惜,如今则是随用随弃,人和物的亲密感也丧失了。”那么在高度碎片化的现实中如何找到值得一写的新东西?格非认可意大利哲学家阿甘本的说法,即我们需要在不同时代重新寻找真正的联系性。
这种真正的联系性区别于现实生活中无处不在的泛滥的联系性(比如人际关系),而是要面向不同时代的深处,凝视不同时代的精神结构,深入思考,进而在这个充斥着大量无意义的文化复制品的时代,努力尝试写出一点不一样的东西。
每次参加完一个热闹的活动,格非总是觉得自己“脑子混乱”,“情感接近崩溃”,回到家中安静一两天,才能缓过劲儿来,“让元神复位”,然后继续读书和思考。“我能享受孤独,在安静和孤独中,你的直觉会告诉你什么是好的”,“总会发生一些意外之事,虽然可能性已被耗尽”,“在安静和孤独中,我们也能更好地看清楚现实性和本然性的关系,如果说马路和红绿灯是现实性,那么大地则是本然性。在本然性面前,现实性不堪一击”。